【作者简介】黄钰晴,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左江流域民族研究中心教师。
【摘要】作为中国民族志电影奠基之作的“民纪片”,开启了中国民族志电影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合作的历史。回溯中国民族志电影合作方式的嬗变,我们可以从一种新的视角梳理中国民族志电影摄制史。中国民族志电影经历了三种不同合作模式变迁。“民纪片”拍摄对象与拍摄者的合作基于对国家行动的共同认同实现;参与式电影的合作模式强调双方的共同参与,在此基础上分化出坚持学者主体性的“二阶电影”与文化持有者主体性的乡村-社区影像。
【关键词】民族志电影;合作;影视人类学史;变迁
在冰天雪地的熹微晨光中,赤膊的猎人起床披衣,狩猎开始……这是杨光海拍摄的《鄂伦春族》影片中的场景。这一场景可能会使人联想到民族志电影的开山之作——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拍摄的《北方的纳努克》。德国学者瞿开森认为杨光海拍摄的风格与弗拉哈迪相似,后者与因纽特人合作拍摄的创作方式,启发了影视人类学者让·鲁什(Jean Rouch)有关“分享人类学(Shared Anthropology)”的价值观念。而包含《鄂伦春族》在内的21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以下简称“民纪片”),被认为是新中国民族志电影的滥觞。
被称为“新中国民族志电影拍摄第一人”的杨光海在叙述“民纪片”摄制经历时,将影片顺利完成归功于当地基层干部与少数民族群众的“通力合作”。在《鄂伦春族》《苦聪人》等影片的拍摄过程中,被拍摄者往往积极配合拍摄者的拍摄工作,形成一种合作的影像摄制关系。在这一基础上,作为中国民族志电影奠基之作的“民纪片”,也开启了中国民族志电影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合作的历史。
拍摄者与拍摄对象的关系是影视人类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发源自弗拉哈迪,由让·鲁什发扬的合作式民族志电影工作方式发展至今,已出现多种不同的模式与形态。弗拉哈迪与爱斯基摩人合作的方式和让·鲁什与尼日尔人合作的方式并不相同,而在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合作方式也几经演变。杨光海与被拍摄的少数民族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显然和今日乡村-社区影像的合作不同。
不同的合作方式,涉及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的关系、推动拍摄进行的动力机制。时至今日,对民族志电影新型拍摄方法的探索方兴未艾,合作式的摄制方法是其中重要的一类。回顾中国1950年代以降的民族志电影发展史,“合作”亦是一条贯穿其中的线索。从杨光海与鄂伦春族的合作开始,回溯中国民族志电影合作方式的嬗变,我们可以跳出拍摄者的单向叙事,以一种新的视角梳理中国民族志电影摄制史。
一、“通力合作”:“民纪片”的共识合作模式
在“分享人类学”的鼻祖《北方的纳努克》拍摄过程中,因纽特人积极配合弗拉哈迪的摄制工作,并为此付出良多,如凿开冰面冲洗胶片,为方便拍摄采光修建比平时大两倍的冰屋,睡在只搭了一半的屋子里。杨光海在小兴安岭拍摄《鄂伦春族》影片时,鄂伦春族人也对摄制组表现出的友好与热情。他们带摄制组一同上山狩猎,赶车运送设备,给断粮的摄制组借粮食。摄制组的摄影机箱意外落水,赶车的鄂伦春族青年立刻趟入刺骨的冰水中打捞机器。“如果说我和摄制组成员拍出了一部鄂伦春族好影片的话,全是鄂伦春族干部和群众支持帮助的结果……鄂伦春族群众对拍摄工作倍加支持,允许我们随时随地跟随拍摄。”
这种支持构成了“民纪片”主要的合作模式。“民纪片”的拍摄由国家财政资助,其实施通常遵循一定的流程:摄制组到了选点地区后,要先向各级党政机关汇报、获得支持,然后通过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的方式,宣传拍片目的意义,“使他们认识到党对各民族的关怀,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从而取得当地人的理解。此后当地人接纳摄制组参与当地生活,建立起较为亲近的互动关系。在拍摄《鄂伦春族》期间,杨光海一行采用反馈法,为鄂伦春族老人播放现场录制下的声音。“我们把录音放给孟可布和几位老人听,他们连连说:‘好,鄂伦春族历史上电影了。’”拍摄双方合作的核心表现是当地人理解摄制组的工作并主动配合,包括进行一系列的主体展演。
另一位“民纪片”参与者蔡家麒追述《鄂伦春族》的复原拍摄过程,“只要将每个场景的主要内容交待清楚被他们领会之后,具体的演示活动则让猎民们自己放手去做,不加干预,不做特别的要求”,猎民与基层干部对此理解程度较高,始终给予积极支持与配合。摄制组对场景内容不做具体安排,给予了当地人一定的主体空间。当地人可在这一空间中根据本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经验进行展演。
但整体而言,被拍摄者能获得的自主空间仍然相对有限。“民纪片”内容大部分是反映当时已经废止或消失了的传统社会中的事物,复原展演是因为拍摄方认为“它们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拍摄方与被拍摄者合作的努力是为了配合“说明‘前资本’社会形态特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发展史基本知识”的目的,合作主导权在拍摄方,被拍摄者需要去理解和琢磨拍摄者想要什么,从而在一定的框架下有针对性地进行表演,使自己所见所知的文化事项转换成拍摄方需要的影像。
这种合作方式是由拍摄方与被拍摄对象的关系决定的。“民纪片”拍摄过程中的拍摄方,并不仅仅是持摄影机拍摄的“拍摄者”。“民纪片”项目由中央政府资助,全国人大民委策划,后实际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代理委托(甲方),国营电影制片厂受委托组建摄制组(乙方),实施影片摄制,摄制行动主要依靠党和政府的行政命令推动。换言之,“拍摄方”包含民族学学者、电影厂摄制组和相关政府部门。“民纪片”摄制作为一项国家资助与主导的“影像民族志运动”,其背后是国家力量的支持。杨光海在对《鄂伦春族》的阐述中清晰地说明了“拍摄方”与“被拍摄对象”的合作形态:“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国家投入了资金,鄂伦春族干部和群众积极参与,民族研究人员和电影工作者同心协力,克服了许多困难。”
拍摄方的“力”集中体现于进入一线拍摄的摄制组,表征于摄影机前。对于少数民族被拍摄对象而言,摄影机这一陌生的新设备无疑是一个闯入者,它引发的刺激不啻于因纽特人第一次见到“两个纳努克”。拍摄苦聪人时,为取得信任,杨光海有时会让当地人看摄影机的取景器。当地人通过取景器看到对面,往往惊讶大喊。而独龙族影片拍摄前期,当地有人害怕拍电影会把灵魂带走。尽管摄制组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和耐心的沟通尽可能地消除了当地人对摄影机的陌生感,但摄影机仍然是一个具有力量的外来物,它和它背后的拍摄方具有不可抗拒的知识与技术权威,是国家行动的执行者,近似于国家的象征。
与因纽特人因为对电影的好奇心而积极帮助弗拉哈迪不同,促使“民纪片”的被拍摄对象与拍摄者合作的是对国家行动的尊崇和认同。为实现合作,摄制组常用的策略是请求当地党政部门派出民族干部协助,开展座谈会,向当地群众说明“民纪片”拍摄这一国家行动的意义,国家在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之前为其保留传统文化生活纪录的善意意图。对于被拍摄者来说,国家的“立此存照”,对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感的确证起到了重要影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与拍摄方的“统一战线”。陈学礼将“民纪片”的拍摄双方视为一个整体,基于完成“民纪片”这一共同目标,民族学研究者、摄影工作者、当地干部、群众四个群体是共同协作的关系,摄制组工作人员也参与“展演”,拍摄者与被拍摄者边界模糊。这一观点忽略了在具体的影片生产实践过程中四者的话语权差异:代表拍摄方的摄制组对最终成片的决定权显然大于当地基层干部群众;而在拍摄方内部,作为委托方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策划和主导了影片的内容生产。但可以确定的是,通过对“抢救性保存”这一国家话语的不断宣讲,“民纪片”将拍摄双方纳入共同体的构建中,形成了一种带有时代鲜明烙印的民族志电影合作方式。
二、“镜头前后”:参与式电影的萌发与分化
杨光海与他拍摄的“民纪片”开启了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合作模式。但这种合作受限于“为科学提供资料”的共识,被拍摄对象的主体性较弱,对于影片内容没有话语权。事实上,作为受委托方(乙方)的摄制组也没有完全的自主权,影片需交由民族研究所专家审核验收。“民纪片”的摄制过程中,杨光海曾采用与鄂伦春族老人分享录音、给苦聪人展示照片和摄影机取景器等方法获得当地人的信任,但由于影片内容的决定权在拍摄方,当地人的反馈无法作用于影片。由于“民纪片”的特殊性质,当地人也无法第一时间观看成片,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杨光海回忆《苦聪人》拍摄结束后,苦聪人“可能没看过(片子)吧,因为我们没有把片子拿下来,中央定的是内部电影,一般人还看不到”。
20世纪中期,让·鲁什与其提倡的“分享人类学”民族志电影合作方法进入大众视野,这种合作方法重要的环节之一,是影片制作者与被拍摄对象共同观看影片,并进行讨论。大卫·麦克杜格(David Macdougall)认为,“他们观看了影片,拍摄者可以做必要的修改、增加以及只有他们参与进来才能做的解释。”也就是说,分享人类学理念中的合作,关键是被拍摄对象的参与反馈,这种反馈会影响电影的生成。这催生了与观察式电影相对的另一种电影风格:参与式电影(participatory cinema)。
大卫·麦克杜格用这个名字称呼那些为拍摄双方提供参与机会的电影。在这种电影中,拍摄者承认自己进入了被拍摄者的世界,并请他们参与电影。这一范畴以让·鲁什拍摄的“真实电影(cinéma-vérité)”为主要范例。按照真实电影的理念,摄影机和拍摄者无可避免地会对被拍摄对象产生影响,承认这种影响、并且展现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的互动关系才是真实。也就是说,拍摄者需要与被拍摄对象进行一种内容上的合作,被拍摄对象的想法主张,会被体现在电影当中。在真实电影的经典之作《夏日纪事》中,拍摄者进入镜头内,不隐藏其在场,被拍摄对象与拍摄者讨论样片,他们的讨论也作为影片的内容加入最后的成片里。这是另一种类型的民族志电影合作方式。
21世纪初,这种合作方式开始被中国的影视人类学者使用。20世纪80年代末,杨光海携“民纪片”作品赴德国交流,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进入开放融合期。1999年,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开始与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IWF)合作,开设了两期项目,联合培养影视人类学研究生,参与教学的导师均为西方影视人类学界的专家,包括让·鲁什的学生芭芭拉·艾菲(Barbara Keifenheim)。
受到这些导师带来的影视人类学理论思想影响,于该项目毕业的一些学员作品多采用参与式的拍摄方法:拍摄前与被拍摄对象沟通自己的意图,不隐藏自己的在场,请求被拍摄对象与自己合作完成影片。如陈学礼在其拍摄的《故乡的小脚奶奶》《回乡偶记》等作品中,均保留了自己与被拍摄对象的对话,且主张“每次把影片做完以后,都要尽快地让被拍摄对象看到”。
这一时期,学者的自我反思使得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的关系得到调整,没有“国家行动”光环加持的摄影机也回归为普通机械。对于人类学者而言,长时间的田野工作与良好的田野关系是建立拍摄双方合作关系的前提,只有被拍摄对象信任他们,愿意合作,他们才可能完成民族志电影的拍摄。这种合作方式在表现特征上较为接近真实电影,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的互动关系成为影片的重要部分,它把拍摄双方都拉入电影之中参与活动,电影不断被反馈给被拍摄对象,被拍摄对象在与拍摄者互动的过程中进行“民族志式展演”。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参与式民族志电影由于主体侧重不同,开始出现分化,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走向。
(一)作为知识生产方式的二阶电影
第一种是坚持人类学学者主体的合作式影像。这一合作方式将影像视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通过学者认知与文化持有者的互动揭示民族志知识生产的过程。鲍江将这一类型的民族志电影称为“二阶电影”:人类学家经过田野完成一部民族志电影后,将这一影片(一阶电影)带回田野与被拍摄对象交流,并将交流的环节记录下来,与一阶作品合体形成二阶电影。鲍江2003年开始的河北娲皇宫田野即为一个二阶电影实践。在这一实践中,作者先以观察式电影的方法拍摄了影片《女娲奶奶的荣耀》,此后携带影片返回田野点,让被拍摄对象观看,并拍摄记录自己与被拍摄对象的讨论,形成作品《我与影片中人物及娲皇宫本地人》与《我与娲皇宫管理部门及本地学者》。换言之,二阶电影所展示的地方性知识,是由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
这种民族志电影合作方式将被拍摄对象的反馈与阐释、被拍摄对象与拍摄者的对话甚至争辩纳入了民族志电影中,使得最终成果兼具研究者与文化持有者的视角观点,打开了民族志知识生产的“黑箱”,将田野调查者调研、认知与求证的过程呈现出来。在20世纪60-80年代的民族志反思浪潮后,传统的文字民族志书写权威被解构,“田野工作中的合作条件成为了民族志中更为明晰的部分”。人类学者与文化持有者合作书写的“二阶电影”,表现出融合理论建构与实践反思的巨大潜力。
影像较文字更容易传递跨文化信息,电视电影媒体的全球化进一步增强了视听语言作为一种普遍性知识的理解基础。蒂莫西·阿什(Timothy Asch)指出,人类学家往往难以和他们的合作对象分享书面出版物,但分享影片却很容易。相比文字民族志作品常常在书写过程中遗漏细节,将人类社会动态变化的文化经验固化为不变的静态结构,民族志影像也更容易通过与当地人的持续互动记录动态的社会文化知识。影像的直观性使得实现这种反馈-沟通具备可能性。
在紧张的仪式进行过程中,文化持有者往往无暇为调查者详细解释其疑问,有拍摄好的影片作为基础,访谈得以更深入地进行。一阶影像传递的信息激发了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记忆,使其能更具体地对某一文化事项进行再观和补充说明。鲍江将在娲皇宫田野完成的一阶影像分享给被拍摄对象程金苗看时,金苗就着影片展现的空间详细解说:“这个上社现在后面八个村……曲峤三奶奶,一点钟往上步行走的都是。”双方对影片内容的讨论、确证,完善了学者对文化事项的认知,加强双方的互相关系。学者亦得以通过观影反馈了解一些难以通过日常访谈获得的微观信息,如文化持有者对某一文化事项的氛围感知与情绪。在《娲皇宫志》中,被拍摄对象赵喜田就表达了对场面不够热闹的质疑,他认为女娲是伟大的神,因而出行的放神枪应该纳入影片中,营造一种隆重的氛围,“一定要观众一看有这样的(感觉)”。
民族志电影镜头需要具备完整性与客观性,这样的学科理念将20世纪中期的民族志电影导向了以冷静观察为基调的“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参与式电影方法背后则是学者对于“客观”的反思。对于不同主体而言,文化事实的客观具备相对性,社会科学学者用以观察和描摹文化的话语逻辑也受到其所在社会的规约。赵喜田的案例,展现了人类学者与文化持有者对文化事实的认知差异。在这一对话中,作为文化持有者的被拍摄对象在观看影片时,更希望影片中的文化事项贴近自己包含氛围感觉在内的主观经验。在上述二阶电影中,文化持有者与人类学者关于“感觉”的对话,突显出人类学跨文化“解释他者解释”的本体特征,也拓展了基于文化参与者具体感知的民族志书写维度。这一走向的参与式民族志电影,更强调学者与被拍摄对象的互动。学者借助参与式电影的形式促使被拍摄对象发挥一定的主体性。二者在不同文化背景基础上的交流常常产生出新的认知,从而更好地完成跨文化知识阐释。
当然,尽管二阶电影设法兼容被拍摄对象的主体性,在这一类型的电影生产合作过程中,被拍摄对象的参与依然有因主体性不足而走向形式化的可能,他们可能会出于摄影机的刺激在镜头前进行表演,也会因为各种社会规范的约束在表达上言不由衷,对拍摄者含糊其辞。他们的行动被摄影机推动。在鲍江的二阶电影作品中,为了让被拍摄对象张水亭参与讨论,拍摄者与其他参与人安抚他“权当没有录像”“可以把这个摄像机忘掉”。拍摄双方显然都清楚,摄影机是一种压力与推力的来源。
而摄影机是作为压力还是推力、被拍摄对象的参与主体性强弱,都与拍摄电影是“谁”的目标有关。二阶电影的合作方式,推动合作发生的是民族志电影的拍摄者,即影视人类学学者。学者为履行自己知识生产的使命,促使被拍摄对象加入对其所处文化的观察与认知行动中,一同完成整个知识生产的流程。当摄像机启动,“电影”借由摄像机显像,刺激与推动被拍摄对象行事。大卫·麦克杜格在1994年讨论参与式电影时,指出真实电影是由电影支配拍摄对象的拍摄形式。它的进阶是参与式电影作为公认的共有目标出现,而另一种尚未被讨论的方式是拍摄者受到被拍摄对象的制约,和他们一同拍摄出影片。在这种形式中,“他者”的主体性将最大化,而作为引导者和中介的学者退居幕后,由原先的被拍摄对象控制民族志电影的内容生产并面向观众。实际上,有关这种合作形式更广为人知的一个概念是“参与式影像(participatory video)”,这一类影像将在下一节进行详细论述。
(二)“共谋共享”的乡村-社区影像
区别于前文提到的“参与式电影”概念,“参与式影像”主要指一种以文化持有者作为主体的工作方法及其成果,“一套使得一个族群或者社区参与到创作与制作他们自己的电影中来的技术”。一般认为西方民族志电影的参与式影像发源于1966年约翰·阿代尔(John Adair)和索尔·沃斯(Sol Worth)的纳瓦霍人电影计划(Navajo film project),以及1967年加拿大电影局推动的“挑战促变革(Challenge for change)”行动,后者具有标志性的项目是知名的福古岛流程(Fogo Process)。
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参与式影像发展于21世纪初,其更为人所知的表述是“乡村影像”或“社区影像”,有学者将其合称为“乡村社区影像”。2000年9月,郭净、章忠云等学者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创办了社区影像教育项目,当地4位藏族村民在人类学者的协助下拍摄了《冰川》等影片,这是中国较早的乡村-社区影像项目之一。此后,这一项目得到了延续。2005年,郭净等人创建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开辟专门的“社区影像单元”对乡村-社区影像成果进行展映。2007年,以此为基础,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启动“乡村之眼”公益影像行动计划,与多地在地组织合作开展乡村-社区影像培训班,逐步发展成为持续性的乡村影像行动,诞生出如《牛粪》《离开故土的祖母屋》等优秀纪录作品。在此后的十余年里,受到“乡村之眼”助力,云南、青海、四川、广西等地均出现了由不同机构组织的持续性乡村-社区影像行动。2013年在“乡村之眼:第三届人类学纪录影像论坛”会议上,参与过相关实践的中国影视人类学者对作为社区行动研究方法的乡村-社区影像进行了理论探索。
中国的乡村-社区影像是影视人类学学者与乡村社区在地居民的合作实验。以“乡村之眼”为据点,郭净、陈学礼、李昕等影视人类学学者将民族志电影的视野和方法带入了多个少数民族乡村社区。这种影像形式颠覆了以往的拍摄者-被拍摄对象的简单关系——以往民族志电影的被拍摄对象拿起摄影机,以往的拍摄者也可能会成为被拍摄对象。随着摄录设备进一步轻便化、智能化,技术门槛进一步降低,拍摄双方的边界变得更为模糊。当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拍摄者,拍摄者与摄像机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也就随之被解构,麦克杜格所言拍摄者受被拍摄对象制约的电影成为现实。受制于社区的礼俗规约,对于作为社区成员的村民拍摄者而言,被拍摄对象往往才是主宰影片走向的人。如广西南丹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的成员在描述他们的拍摄过程时,就提到他们曾多次因被拍摄对象的主张而改变拍摄内容。
而在这种民族志电影的生产流程中,拍摄者-被拍摄者并非全部。乡村-社区影像的合作关系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关系:影视人类学者与拍摄者,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影视人类学者提供的理念与技术使得在地村民拍摄的影像得以跨出其本文化的视角。事实上,正是学者与拍摄者的合作使得这一类参与式影像成为民族志电影。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的合作关系则为这种民族志电影提供了一种内部的自观视角。这达成了分享人类学的另一层含义:共享电影创作的知识。提出这一概念的让·鲁什一直期待他的合作者们能够制作自己的影片,独立地发出他们的文化声音。
乡村-社区影像的生产动力亦与前两个阶段的民族志电影生产不同。项目制的乡村-社区影像起初是为项目方的需求而进行,如福特基金会对妇女卫生的关注,但随着时间推移,能长久存续的项目大多依赖于乡村社区的需要。村民需要这些“摄影师”为其记录婚丧嫁娶等人生仪礼,完成社区的共同目标:保留传统文化知识,或是宣传旅游产品。非项目制的乡村社区影像,更是应社区的需要而生,当村民需要拍摄婚礼,就有人成为婚礼摄影师;村民想听山歌,就会有人拍摄山歌对唱;拍摄生态影像的青藏高原牧民,希望借影像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原……从这一角度看,在乡村-社区影像的合作关系中,被拍摄对象与拍摄者共同谋划了影像的生产,被拍摄者的需求主导了影片内容。在这一机制推动下的民族志电影摄录过程也是一种知识生产,其成果更接近于费孝通所主张的“有用的知识”,即处于文化持有者的立场、对其有益的知识。
对于使用摄影机拍摄自身生活的村民拍摄者而言,这种动力机制更为明显,他/她的拍摄完全基于自身(也就是被拍摄对象)的需要,为达到保存家庭影像记忆或推广自家农牧、文化产品等目的而进行。
随着影视设备的资金技术门槛被智能手机打破,摄影机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可以吸引封闭地区猎民和牧民崇拜与投入的神圣物。“祛魅”的摄影机成为一种可以服务文化持有者的工具。在某些情况下,当文化持有者需要影视人类学者与其共同完成民族志电影时,会出现一种新的“共谋共享”合作形态。
2018年,笔者曾作为兰州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成员随团队前往肃南明花拍摄当地裕固族的一个特殊节日:东迁节。这一节日作为一种对于祖先的集体记忆存在于裕固族的传说故事中,其历史存在尚待考据。2016年,明花的裕固族人决定要恢复这一节日。此时兰州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负责人王海飞已在当地田野多年,参与了当地人对节日筹建的讨论。当地建立东迁节筹办组委会,旋即邀请实验室团队前来拍摄东迁节。在此之前,当地裕固族民族精英已从口头文学与历史文献中找到作为节日核心的迁徙传说,邀请与他们相熟的民族志电影工作者对节日进行拍摄,是希望借助摄影机进一步确证“东迁节”的合理性和意义。借用当地裕固族头人GQ的表述,以影像记录节日程序是“把它固定一下”。民族志电影可以作为一种族群共同的影像记忆建构并巩固其文化传统,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视听互惠”(Contredon Audiovisuel)。民族志电影拍摄者因想要记录与研究文化造型过程而协助了被拍摄对象的文化建构,双方共享其成果。换言之,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通过摄影机“共构”了一个节日,一种较为稳定的影像群体记忆。
结语
按拍摄双方关系与合作动力,可将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合作方式划分为三种:以为国修史为共同目标、由拍摄方主导的民纪片模式;参与式影像的两种不同模式——以知识生产为目标、由学者推动的二阶电影和以社区建设为目的、由被拍摄对象主导的乡村-社区影像。
从“民纪片”的“通力合作”到参与式影像的“共谋共享”,这三种合作方式是经过两次嬗变与分化形成的。
杨光海等“民纪片”的先驱拍摄者,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套民族志电影的合作方法,这种合作改变了新中国建立前我国民族地区长期在影视作品中被外来者单向凝视的状态,使被拍摄者呈现出一定的主体性,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当家做主”的叙事号召相呼应。在这种合作模式中,摄制由拍摄方主导,合作动力是双方对国家及国家行动的认同。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合作方式完成了第一次嬗变,出现了参与式电影。学者的反思促成了参与式合作模式的出现,拍摄者开始进入镜头,与被拍摄对象处于相对平等的位置进行合作,合作程度取决于双方的关系,被拍摄对象的主体性开始显现。
参与式电影分化出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一种是保留了拍摄者主体性的“二阶电影”,这一类影片由影视人类学学者发起摄制,在满足学者研究目的基础上用摄像机激发被拍摄对象的主体性,从而进行可持续的合作式知识生产。21世纪初出现、发展至今的乡村-社区影像则踏上了另一条分化路径,影视人类学者退隐,转而为从前的“被拍摄对象”——文化持有者提供理念与技术支持,学者的思维和观察借助培训隐藏于文化持有者的拍摄行动中。影视技术的“祛魅”、被拍摄对象与拍摄者角色更高的可转换性,带来了被拍摄对象主体性的大幅度提升,影像的合作摄制往往由被拍摄对象主导。这一类型的合作方式的另一表现形态是:在乡村-社区影像尚未普及的地区,文化持有者借助民族志电影工作者的力量介入,推动本社区乃至本族群的文化记忆建构与传承。
中国民族志电影合作方式的嬗变与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与电视电影制片业的体制改革,民族志电影生产进入多方参与时期。在开放大潮中,中国与国际影视人类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引入了当时西方影视人类学的前沿理念。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与技术的快速发展,摄制设备逐步轻便化、智能化和平价化,影像生产的入门成本不断降低,都是促成嬗变的社会背景。而更重要的是,中国民族志电影工作者一直在本土田野实践中不断地思考求索。
而今,影像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的合作关系已经全然被改写,新的民族志影像书写方式正在展开。当我们回溯这种合作关系的变迁,“民纪片”时代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尽管合作模式是拍摄方主导的,但通过建立共识与紧密的田野关系,它奠定了民族志电影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合作的基础。正如杨光海所言,这些影片是通力合作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化持有者的理解与参与,这一批“民纪片”不会记录下这么丰富的文化细节。而这些影片完成之后,又成为文化持有者也共同享有的影像记忆——小兴安岭许多鄂伦春家庭都收藏有《鄂伦春族》的影碟。当杨光海感动于鄂伦春人的热情勇敢,他镜头下的山林游猎世界也就成了整个鄂伦春族群可以深情回望的记忆底片。这样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互惠,正是民族志电影“合作”的题中之义。而观察与探索摄像机前后的人与他们的关系,也是我们未来仍然要持续关注的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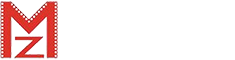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7870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7870号